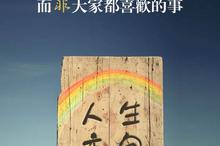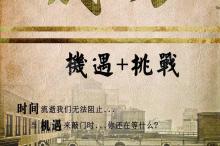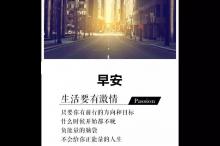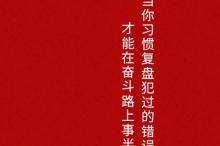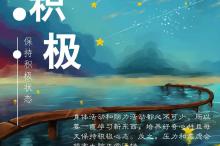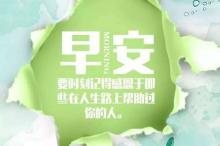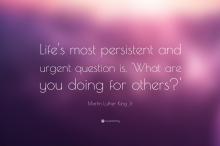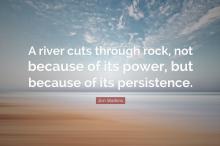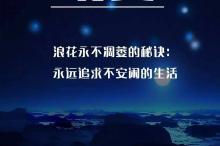“一束光”,可以有多亮?照多远?
武汉·中国光谷,
这里,诞生了我国第一根石英光纤,从此创新涌动,聚光成谷。
这里,十年间,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,为科技创新指明方向,寄予殷切期许。
从武汉“地图外的两厘米”到“独树一帜”的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,一代代光谷人,以光为引、追光而行,用科技自立自强锻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名片。


光纤,数据传输的“高速公路”。
2023年,早春,料峭轻寒。但在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长飞”)的光纤拉丝车间里,拉丝炉的温度却高达2000℃。近5层楼高的拉丝塔中,晶莹透亮的光纤预制棒悬于顶端,经过“炙烤”,均匀熔化。塔顶到塔基30多米的落差间,从“棒”到“丝”,时速210公里的拉动中,一根10000公里长的光纤被拉制出来。
长飞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此生难忘的一个场景,发生在2013年7月21日的那个下午。“习近平总书记当时问我,你们的‘长飞梦’是什么?我说,用6到8年时间做到这个领域的全球第一。总书记又问,为什么有这个‘长飞梦’?我说,如果中国每一个行业,都有企业做到全球数一数二,那么我们的国家,也必定会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大国和经济强国。”
沿着细如发丝的光纤,回溯故事的起点。
1970年,全球第一根光纤在美国诞生。6年后的一个春天,大洋彼岸的中国湖北武汉,南望山脚下的一个简陋的实验室里,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年轻人,带领团队,拉出一根长度为17米的“玻璃细丝”,这也是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。3年后,他们又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、每公里损耗只有4分贝的光纤。
这个年轻人的名字,叫赵梓森。

△赵梓森(左二)与同事们一起做实验
随后几年,苦苦研究,赵梓森深深感悟:“只有引进外国设备,才能加快研究速度。”为了实现大规模量产,赵梓森力推合资建厂。但接二连三,美国、日本等光纤制造强国拒绝了中国。经过艰苦谈判,终于在1985年,荷兰飞利浦公司与中方达成协议,合作建立中外合作公司——长飞公司。
长飞,“长江边的飞利浦”。
1988年5月,带着“用市场换技术”的时代印迹,长飞正式成立。世纪之交,长飞接连七次扩产,2002年,光纤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万芯公里,成为全球主要光纤光缆生产企业,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依赖进口建设国家光缆通信干线的历史。
仅仅引进、吸收技术还远远不够!不甘心做“外国工厂”,管理层想立项增加研发资金投入,董事会不予批准。此时,某国际知名公司一改以往不愿向中国输出技术的姿态,主动抛出“橄榄枝”,但前提是合作后长飞只能生产多模光纤,放弃研发市场亟需的单模光纤。
长飞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回忆:“关键技术是不可能依靠市场‘换’来的,长飞必须搞自主研发,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!”困难之际,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雪中送炭,支持长飞3000万元资金。抗住内部压力,抵御外部“诱惑”,2001年,长飞成立了专门的研发中心。此后,无论市场好坏、行业周期起伏,每年都保持不低于销售收入5%的研发投入。

△长飞自主研发生产的光纤预制棒
科技创新,一靠投入,二靠人才。
古有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,在光谷,也流传着一段“马新强月下追闫大鹏”的佳话。
激光,被誉为“最快的刀、最准的尺、最亮的光”。2000年左右,国外的设备“削铁如泥”,国内的却是“小儿科”,大多应用于低端制造,切割木头。激光器之于激光装备,就像芯片之于电脑。
2006年,掌握光纤激光器核心技术的闫大鹏从美国来汉参加华创会,为了留住他,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一路“追”到了北京。“我当天晚上就回到北京,准备第二天就回美国。然后马总是出差回来,连夜赶到北京,在招待所跟我谈签的合同。”锐科激光副董事长、总工程师闫大鹏回忆。

△华工科技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智能装备
2007年4月,51岁的闫大鹏与华工激光合资创立锐科激光,仅用一年时间,就研发出国内首台10W脉冲全光纤激光器。但是,当时国外已经研制出了更高规格的10kW激光器。进口一台要花700万人民币,再做成激光加工设备,费用高达1000万。历经6年攻关,锐科激光终于研制出了国内首台10kW工业级光纤激光器,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此项技术的企业。
武汉·中国光谷,在世纪之交的全国“光谷热”中,只是“七分之一”。
大浪淘沙。“中国光谷”,只有最终坚持下来的武汉,实至名归。

△光谷中心城俯瞰图
2013年7月,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来到光谷考察。
“我们走出了一条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的路子,这些‘土枪土炮’比‘洋枪洋炮’效率更高!”长飞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自豪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。
习近平总书记说:“我们这么大的国家,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。一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。”
令旗已扬,方向即定。追“光”之路,奋发不休。

古有“烽火狼烟”,在守不在攻。
脱胎于武汉邮科院的烽火科技则自带家国使命,剑指世界一流。